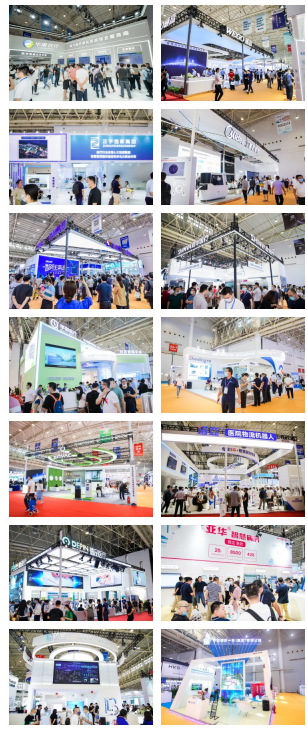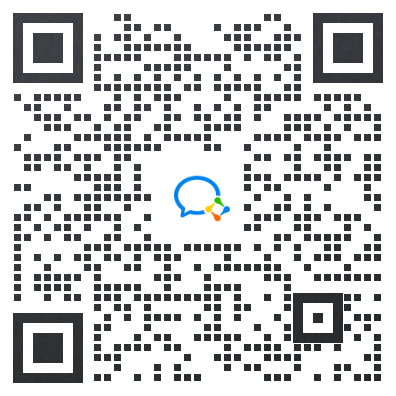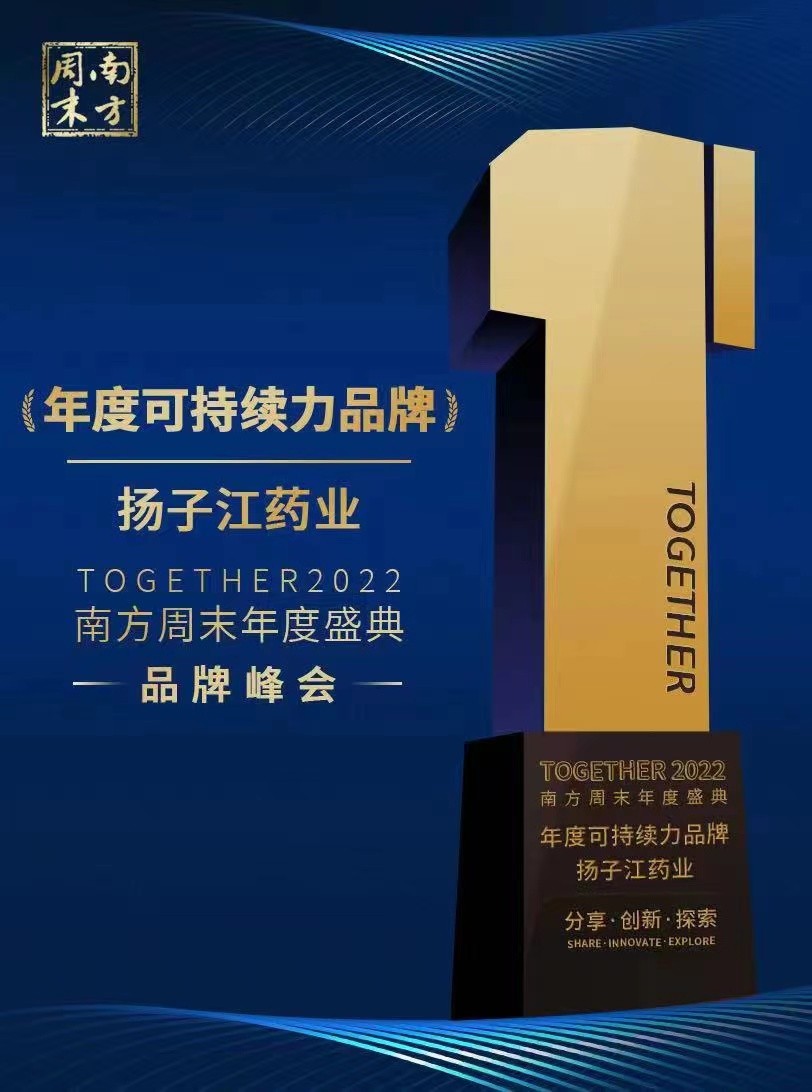引言
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理念、情感追求、审美意识的载体和投射,而这一切又都是通过对作品主人公的塑造体现出来的。
曹雪芹的女性意识,就渗透在他所描写的男女主人公的性格和他们的命运遭际中。林黛玉无疑是大观园众多女儿中第一个叛逆者。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她虽生就了一副“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临风”的纤弱之躯,但是其为人处世、性情表现,却全无半点卑弱色彩,与女子“四德”的道德要求相去甚远。
林黛玉自幼失母,之后又丧父,寄居于外祖母家。
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本应使她学会察言观色、装愚守拙、息事宁人、随遇而安的弱者的生活技巧和态度。
然而林黛玉偏偏却养就了一颗过于敏感和自尊的心,对于一切她自认为是伤害了自己尊严或利益的人和事,她都毫不留情地以犀利甚至尖刻的语言予以反击。
这种常常把人置于槛尬境地的“辩口利辞”,导致了她在贾府中的孤立和少友。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正是林黛玉的生活感受的真实写照。在女工方面,林黛玉亦不擅长。
其幼小之时,由于父亲膝下无儿,又因她聪慧过人,父亲便将她像儿子一样严师教读。
寄居贾府之后,贾母年事已高无暇顾及,他人如王夫人者隔着一层更不便管教,因此林黛玉虽还不至于到了不知针线纺织为何物的地步。
但却不像一般闺中女儿那样,以针线纺织为自己的每日要事,相反,却是以读书吟诗为乐。
在《红楼梦》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林黛玉拈针作绣的描写,却对林黛玉用自己的心灵血泪吟咏的诗篇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一首哀艳绝伦的《葬花词》博得了多少古今读者内心的共鸣。
但对于林黛玉而言,她最不能见容于封建道德的,却是她对于自由爱情的执着无悔和至死不渝的追求。
贾宝玉是林黛玉在诺大一个贾府中的惟一知己,她和宝玉不仅是两小无猜自幼耳鬓厮磨一起长大,而且是精神、性灵和情感的相契。
她从不劝宝玉去追求仕途功名,更不以宝玉的性情行为为怪,正是在这一点上,她真正赢得了宝玉的爱。
她对宝玉的惟一次劝导是在宝玉被打之后,此时的她“气噎喉堵”,
“你可都改了吧!”
而宝玉听后却“长叹一声”道,
“你放心,别说这样话。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
让黛玉“放心”,是深知黛玉鄙弃世俗,在这样的时刻,仍如此坚持他们对精神的追求,宝玉不可谓不令人起敬。
而宝黛之心与心的相契、灵与灵的交融,也就不难想知了。林黛玉以一生的泪水和情感去追求自己的爱情。
作者以极细腻感人的笔墨描绘了这位生活于十八世纪的贵族少女为爱情而经历的炼狱般的感情煎熬和精神痛苦。
林黛玉虽非以“三从四德”为自己的生活教条,但男女婚姻爱情上的传统道德规范仍深深影响和束缚着她的心灵。
“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对于她仍是难以决然冲破的樊篱。
她常自怨自叹父母早逝不能为她的婚姻作主,她寄希望于贾母,盼贾母亲上作亲为自己定下与宝玉的婚事。
一方面她希望宝玉将心与她,专情于她,但另一方面,当宝玉两次借曲词向她试探表白时,她却“桃腮带怒,薄面含嗔”,指责宝玉“该死”、“胡说”!并扬言要告诉舅舅、舅母去。
但是可贵的是黛玉最终并没有屈服于礼教,她抗争着——既与命运抗争,也与自己内在化了的伦理道德抗争。
她虽指责宝玉弄来“淫词”艳曲“欺负”她,但内心里却对这些表现争取自由爱情的戏曲极为欣赏,爱不释手,甚至“默默记诵”。
宝玉被打之后曾遣晴雯给她送去两块旧帕,黛玉体会到了这旧帕所蕴含的深情,竟然一时情动。
旧帕题诗是世间至情儿女心盟的明证,这也表明了黛玉已经挣脱了内在伦理对自己的约束而向着精神自由的境界迈出了重要一步。
然而,黛玉痴情的最动人处,乃在于她最终敢于蔑视伦常道德,而以一死来证明自己爱情的纯洁和不可侵犯。
“焚稿断痴情”是林黛玉对于社会和家族的封建压制的无言控诉和鞭挞。
如此一个不屈服于命运、以自己的纤弱之躯去与整个家族和社会抗争的女子,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作为黛玉的惟依靠的贾母,她心里自然很清楚,“心病”靠药是治不好的,解铃还需系铃人。
然而她虽平日疼爱林黛玉,但是对于林黛玉追求自由爱情这件事却决不宽容饶恕,一句“我也没心肠了”,透出了多少残忍和冷酷!
况且,以黛玉的多病之身和处处有违“四德”的作为,贾母也是断然不会让步做出选择黛玉作为宝玉之妻的决定的。
而不让步,林黛玉则必死无疑,它正应了第八二回林黛玉的那个不祥之梦。
在梦中,黛玉被置身于最绝望无告的困境,她声嘶力竭地向贾母等人求救哀诉,甚至表示愿意“,
情愿自己做个奴婢过活,自做自吃”
也换不来贾母的一丝怜悯。
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看,梦是个人潜意识的一种流露,那么对于林黛玉,这实在不能说只是一种潜意识,而是她“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反映,是她对于贾母的一种本能直觉。
林黛玉为爱情而死,作者以她的悲剧展示了封建社会对于一个追求自由爱情的美丽女性的无情摧残。这当然是作者的深刻之处。
但是作者更以他独到的视角,向世人展示了生,活在封建社会男权文化之下的全体女性的悲剧。
作者通过贾宝玉之口,予以了彻底的否定。贾宝玉认为,
“天生女儿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
宝玉之言虽有童稚之气,但从全书的描写看,却是宝玉从自己短暂的红尘生涯中得来的真实体验和领悟。
《红楼梦》第5回写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警幻仙子以茶、酒款待,茶名为“千红一窟”,酒名为“万艳同杯”。
这是曹雪芹对天下女子终不能逃离其悲剧命运的一个象征性喻示。
然应该指出的是,这里的“红”与“艳”,只是对于女儿而言,最多也只包括已出嫁但尚未成为“鱼眼睛”者。
因为有价值者的毁灭,方可令人为之扼腕叹惜,而如“鱼眼睛”的毁灭,在曹雪芹看来或是从贾宝玉所表现出来的感情意识来判断,是断不可称其为悲的。
一声“比男人更可杀”的怒斥,便可足以证明。
而“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无有老妇人人于其中,亦可为一证。
人“正册”者为以林黛玉、薛宝钗为代表的小姐辈,人“副册”者为以香菱为代表的美妾辈。
人“又副册”者为以晴雯、袭人为代表的丫环辈,她们又总归于“薄命司”中。
这表明,作者从宿命的意识出发,深刻感悟到了天下女儿,无论其出身高低贵贱,也无论其对社会的文化道德规范认同与否,最后都落得一个殊途同归的命运。
而贾宝玉则是从女儿们的身上看到了生活的真谛,体验到了生活的乐趣,因此他抛弃了男尊女卑的道德教诲,也抛弃了主子奴才有别的等级观念。
他尊重女儿的人格,欣赏女儿的才华,探春倡建诗社,他热烈欢呼,积极支持,而每次评诗被列于末等,却又心悦诚服,全不因落在了女儿之后而心存芥蒂。
他对大观园中的女儿几乎都表现出了不同层次的关怀,乐于为她们“充役”,甚至到了忘我的地步。
看见龄官画“蔷”,他心中便生出无限的怜惜,
“这个女孩子一定有什么说不出的大心事,才这么个样儿……看他的模样儿,这么单薄,心里哪里还搁得住煎熬呢?可恨我不能替他分些过来!”
大雨骤降,他竟浑然不觉自己也被淋湿,还只为那个女孩子担心,
“这是下雨了,他这个身子,如何禁得住骤雨一激?”
这件后来被外人传为宝玉痴呆的小事,却反映出了宝玉对于女儿一片真诚无私的爱。
这样的痴呆“作小”行为,与传统道德所主张的男尊女卑是何其大相径庭!
曹雪芹先进的女性观,他与传统男性至上文化的抗辩,正由他对于贾宝玉形象的塑造中体现了出来。
但是曹雪芹的可贵,不仅在于他通过贾宝玉和一系列女儿形象的塑造,让读者看到了女性的本来之质的美和高尚,而且还在于他让读者看到了女儿的本来之质的如何失落。
这里的女性变论,看似荒唐可笑,实却切中要害。
女子一旦出嫁,从夫事夫为夫所御的角色要求,使她只能够规规矩矩地以“三从四德”为事,做一个贤妻良母,方能为社会、家族和丈夫所接受。
任何的逾道德规范雷池一步,都有可能招致被休弃的大祸,而被休弃的女子,还能期望后半生有幸福吗?她只能在人们鄙弃的目光中忍辱负重终其一生。
参考文献
《红楼梦》《脂砚斋评批红楼梦》《红楼梦人物论》王昆仑-
 红楼梦中的对比,天下女儿悲剧命运殊途同归,曹雪芹有何深意?|最新消息引言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理念、情感追求、审美意识的载体和投射,而这
红楼梦中的对比,天下女儿悲剧命运殊途同归,曹雪芹有何深意?|最新消息引言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理念、情感追求、审美意识的载体和投射,而这 -
 神舟十五号返回舱着陆,带回了拟南芥微重力研究样品 世界热闻北京时间6月4日6时33分,神舟十五号飞船返回舱在酒泉东风着陆场成功着
神舟十五号返回舱着陆,带回了拟南芥微重力研究样品 世界热闻北京时间6月4日6时33分,神舟十五号飞船返回舱在酒泉东风着陆场成功着 -
 【全球快播报】科技之伞护佑航天员天外归来6月4日清晨,万众期待中,一顶红白相间的大伞如约绽放,守护着神舟十五
【全球快播报】科技之伞护佑航天员天外归来6月4日清晨,万众期待中,一顶红白相间的大伞如约绽放,守护着神舟十五 -
 董卓怎么死的1、司徒王允设反间计,挑拨董卓大将吕布杀死董卓,结果成功。初平三年
董卓怎么死的1、司徒王允设反间计,挑拨董卓大将吕布杀死董卓,结果成功。初平三年 -
 全球球精选!淋浴间吊顶高度(淋浴房离吊顶10公分闷吗)相信大家对淋浴间吊顶高度,淋浴房离吊顶10公分闷吗的问题都很疑惑,这
全球球精选!淋浴间吊顶高度(淋浴房离吊顶10公分闷吗)相信大家对淋浴间吊顶高度,淋浴房离吊顶10公分闷吗的问题都很疑惑,这 -
 天天滚动:唐山陶瓷集团(关于唐山陶瓷集团的基本详情介绍)唐山陶瓷集团,山陶瓷集团的基本详情介绍很多人还不知道,那么现在让我
天天滚动:唐山陶瓷集团(关于唐山陶瓷集团的基本详情介绍)唐山陶瓷集团,山陶瓷集团的基本详情介绍很多人还不知道,那么现在让我 -
 襄阳入选全国第三批海绵示范城市|环球视讯襄阳入选全国第三批海绵示范城市---湖北日报讯(记者雷闯、吴宇睿、通
襄阳入选全国第三批海绵示范城市|环球视讯襄阳入选全国第三批海绵示范城市---湖北日报讯(记者雷闯、吴宇睿、通 -
 可以下树了?沙特公报:梅西将在48小时内抵达利雅..._天天头条可以下树了?沙特公报:梅西将在48小时内抵达利雅得加盟利雅得星月根据
可以下树了?沙特公报:梅西将在48小时内抵达利雅..._天天头条可以下树了?沙特公报:梅西将在48小时内抵达利雅得加盟利雅得星月根据 -
 cad坐标标注样式设置参数_cad坐标标注样式设置1、cad坐标标注设置字体的步骤如下:1 输入D空格进入标注样式管理器。2
cad坐标标注样式设置参数_cad坐标标注样式设置1、cad坐标标注设置字体的步骤如下:1 输入D空格进入标注样式管理器。2 -
 《逆水寒手游》行刑长解锁玩法在逆水寒手游中会有很多的身份可以去解锁获得,还会有一些是隐藏身份,
《逆水寒手游》行刑长解锁玩法在逆水寒手游中会有很多的身份可以去解锁获得,还会有一些是隐藏身份, -
 高考期间,我省平均气温与常年接近,降水稍多4日,中国吉林网从省气象局获悉,预计高考期间(6月6-8日),全省平均
高考期间,我省平均气温与常年接近,降水稍多4日,中国吉林网从省气象局获悉,预计高考期间(6月6-8日),全省平均 -
 六五环境日·守护好一江碧水|最美环保铁军!获奖名单发布 全球独家编者按:6月4日,湖南省生态环境厅、省文明办与岳阳市委、市政府共同主
六五环境日·守护好一江碧水|最美环保铁军!获奖名单发布 全球独家编者按:6月4日,湖南省生态环境厅、省文明办与岳阳市委、市政府共同主 -
 杭州吃饭最大的问题倒不是贵,而是不好吃杭州吃饭最大的问题倒不是贵,而是不好吃。你看着大众点评上的高分店,
杭州吃饭最大的问题倒不是贵,而是不好吃杭州吃饭最大的问题倒不是贵,而是不好吃。你看着大众点评上的高分店, -
 全球焦点!广西首份RCEP项下输菲律宾原产地证书和声明签发6月3日,南宁海关介绍,《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菲律宾实
全球焦点!广西首份RCEP项下输菲律宾原产地证书和声明签发6月3日,南宁海关介绍,《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菲律宾实 -
 魔兽世界怀旧服花羽鹦鹉哪儿出_魔兽世界花羽鹦鹉在哪刷1、东部大陆荆棘谷的海盗怪身上有几率掉落。本文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魔兽世界怀旧服花羽鹦鹉哪儿出_魔兽世界花羽鹦鹉在哪刷1、东部大陆荆棘谷的海盗怪身上有几率掉落。本文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
 世界看热讯:北京现代沐飒 MUFASA将于6月中旬上市 预售13.98万元起易车讯 我们从官方渠道获悉,北京现代沐飒MUFASA将于6月中旬上市。作
世界看热讯:北京现代沐飒 MUFASA将于6月中旬上市 预售13.98万元起易车讯 我们从官方渠道获悉,北京现代沐飒MUFASA将于6月中旬上市。作 -
 三星r429笔记本加内存条(三星r429笔记本)_全球速讯来为大家解答以上问题,三星r429笔记本加内存条,三星r429笔记本很多人
三星r429笔记本加内存条(三星r429笔记本)_全球速讯来为大家解答以上问题,三星r429笔记本加内存条,三星r429笔记本很多人 -
 策展的能量与引擎作用策展的能量与引擎作用原标题:策展的能量与引擎作用近日,“策展在中国
策展的能量与引擎作用策展的能量与引擎作用原标题:策展的能量与引擎作用近日,“策展在中国 -
 意大利金融专家:美债危机影响他国金融稳定 去美元化加速-天天热点评意大利金融专家:美债危机影响他国金融稳定去美元化加速,金融,美债,意
意大利金融专家:美债危机影响他国金融稳定 去美元化加速-天天热点评意大利金融专家:美债危机影响他国金融稳定去美元化加速,金融,美债,意 -
 【热闻】抖音励志经典句子_抖音励志经典句子像知道你明天就要死一样的生活,像你将永远活着一样的学习。乐观者看到
【热闻】抖音励志经典句子_抖音励志经典句子像知道你明天就要死一样的生活,像你将永远活着一样的学习。乐观者看到 -
 中信银行网上银行查询_中信银行网上查询1、中信银行泰州分行没有官网。2、每个银行的官网都是由总行统一开通,
中信银行网上银行查询_中信银行网上查询1、中信银行泰州分行没有官网。2、每个银行的官网都是由总行统一开通, -
 世界快报:网络很好但是b站很卡_b站很卡1、这个跟你的宽带有关系,长城应该是没有自己的互联网出口的,通常是
世界快报:网络很好但是b站很卡_b站很卡1、这个跟你的宽带有关系,长城应该是没有自己的互联网出口的,通常是 -
 法网-萨巴莲卡2-0轻取希玛 斯蒂芬斯梅尔滕斯进第三轮其他比赛中,美国名将斯蒂芬斯6-2 6-1轻取格拉乔娃,梅尔滕斯6-3 7-6战
法网-萨巴莲卡2-0轻取希玛 斯蒂芬斯梅尔滕斯进第三轮其他比赛中,美国名将斯蒂芬斯6-2 6-1轻取格拉乔娃,梅尔滕斯6-3 7-6战 -
 全球时讯:多孩家庭购买改善型住房可否有贷款利率优惠?央行上海总部回应近日有市民提出,大多家庭在生育之后会面临住房面积不足的问题,购买改
全球时讯:多孩家庭购买改善型住房可否有贷款利率优惠?央行上海总部回应近日有市民提出,大多家庭在生育之后会面临住房面积不足的问题,购买改 -
 千百度歌词_千 百 当前速读1、千方百计、千锤百炼、千补百衲、千娇百媚、千奇百怪、千疮百孔、千
千百度歌词_千 百 当前速读1、千方百计、千锤百炼、千补百衲、千娇百媚、千奇百怪、千疮百孔、千 -
 天热也得戴 戴了能保命_全球快看嫌热不戴盔摩托车驾驶员被拦停教育
天热也得戴 戴了能保命_全球快看嫌热不戴盔摩托车驾驶员被拦停教育 -
 遂川县气象台更新暴雨红色预警信号【I级/特别严重】【2023-06-03】-天天消息遂川县气象台2023年06月03日02时07分变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
遂川县气象台更新暴雨红色预警信号【I级/特别严重】【2023-06-03】-天天消息遂川县气象台2023年06月03日02时07分变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 -
 伊犁马价格_伊犁马1、伊犁马在目前市场上的价格参差不齐。2、以年龄来说了。3、3-5岁的体
伊犁马价格_伊犁马1、伊犁马在目前市场上的价格参差不齐。2、以年龄来说了。3、3-5岁的体 -
 增仓近1倍!外资突然爆买这家公司,白酒却被卖超56亿!发生了什么?本周,是5月的结束,也是6月的开始,受市场疲软影响,北上资金5月净卖
增仓近1倍!外资突然爆买这家公司,白酒却被卖超56亿!发生了什么?本周,是5月的结束,也是6月的开始,受市场疲软影响,北上资金5月净卖 -
当前视点!猪肉怎么保鲜 新鲜猪肉怎么保鲜1、可以把毛巾用醋浸湿后,然后将没有吃完的鲜肉包起来,然后放在一个背风的地方,以免醋风干,这样,也可